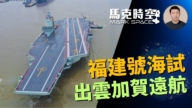【新唐人2014年1月1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一九六零年四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五千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二十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二十二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一九六零年八月以来,有四千人患病,八、九两月死亡一百五十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八千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六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九十三个,动用国家资金四百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一九五九年冬起,连续搞了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二百五十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一千二百七十人,其中被折磨死的一百二十四人,致残八十五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十三-二十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一九六零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八千多元。(注十)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五九事件”),是一次以十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六十点五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五十六点五七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十八个人民公社,下设一百三十六个管理区,七百七十六大队,五千九百零一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初,历时五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十二点四五一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强,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二千九百三十八户,遗下的孤儿寡崽四千七百三十七人,外出逃生的农民四千七百三十七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十六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一九五九年粮食只收了三点二二亿斤,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八点四六亿斤,虚报五亿多斤。为了兑现八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一千二百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十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十二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一九六零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宴乐斌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样一见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九月十六日傍晚还有四十八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四十八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交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四十七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两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四十七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件事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注十一)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一九六零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十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二千七百九十四人(经批准的有六十五人),关死的就达二百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十万民工(实际集中七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十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一九六零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五十一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一九六零年四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三十六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打伤致残的一百七十五人,关押死的二百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一千六百八十人。
一九六零年四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二百五十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二至三个,住院病号六千三百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二十三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一所,把四千七百三十五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六个,占公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三十一个,组织不纯的五十一个,共八十二个,占管理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点三;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三百七十七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一九六零年六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一九六零年八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一九八三年三月平反); 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三十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完全推给下面。(注十二)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一九六零年六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注十三)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六盘水地区灾情也很严重。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日,宴乐斌三人经由水城县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他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他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注十四)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一九六一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注十五)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注解:
[注十] 《中纪委大事记》,《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零]一零三六号转发。
[注十一] 宴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载《炎黄春秋》二零一二年第五期,第五十八页。
[注十二] 刘兴盛:《历史的悲剧 沉痛的警示——一九五九年贵州省“湄潭事件”始末》,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七年第十一期。
[注十三] 郑义:《大跃进时期农村悲剧:江口事件梗概》,香港《争鸣》,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注十四] 宴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载《炎黄春秋》二零一二年第五期,第五十九页。
[注十五]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十月号。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