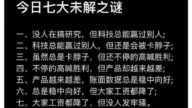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新唐人2010年8月3日訊】近年來聽到中共當局活摘法輪功學員的指控。有的報告中提到有時劫掠器官的醫生竟然不施麻藥活活開膛……。世人震驚之餘,仍是不能置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會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場面。而我在那件往事發生后近四十年,我才第一次聽父親說起。
作為家族中的長孫,我為了父親的心愿,今年春天第一次隨父母赴印尼祭祖掃墓、拜訪親朋。在萬隆的一家名叫梔子花的餐館里,父親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那段荒唐往事,令在座眾人不寒而慄。父親一向不善言辭,但這次訪佛變了一個人。說到動情之處,聲情並茂,唏噓不已,彷彿重歷那段刻骨銘心的往事。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亞,十幾歲便懷著滿腔激情搭輪船返回祖國。一踏上赤土便趕上史無前例的大飢荒。飢餓、疲勞、緊張加上一波一波政治運動帶來的種種壓力,使他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剛剛三十歲出頭父親便不得不接受胃切除的大手術。
那時正在文革之中,手術當天醫生告知父親要實施「政治麻醉」,那是當時對針灸麻醉的代名詞。您聽說過政治麻醉嗎?那麻醉不是心理上的,也不是生理上的……。
在那個所有事物都被政治化了的年代,針灸也在所難免。狂人毛澤東主張走中西醫結合的路,於是所有的醫療系統紛紛響應,以針灸代替麻醉劑是其中的一個項目。在父親住進的那家醫院,病人是接受常規麻醉還是針灸麻醉依據的不是病人的身體狀況或手術類型,而是實施手術的時間。每周有固定的一天或幾天必須按政治需要實施針灸麻醉,這就是政治麻醉的由來。
據醫生說,針灸麻醉在胸肺外科手術中已經取得初步進展,其中原因之一是肺葉 神經末梢比較少,對痛覺不敏感。但實施腹腔手術還完全沒有把握。年輕的父親被選作首批試驗品之一。主治大夫在察看了父親的身體之後,叮囑針灸師要把針下的深一些,因為好運動,善游泳的父親腹肌很厚很發達。手術當天,父親的手、腳都被皮帶固定住,頭頸也同樣被固定,眼睛也被嚴嚴實實地遮住,以防備政治麻醉無效。醫生還特意準備了一條毛巾給父親咬,以防止咬壞牙齒或舌頭。我無法想象這樣躺在手術室里他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恐怕不是緊張、恐懼這幾個詞語所能形容的。
故事的結局大家應該可以猜到。我也不知如何用簡單的詞彙描述那其中的具體過程和感受。我只記得父親在講述往事時,他如霜如雪如根根銀針似的白髮,似乎每一根都在顫抖,每一根都在吶喊。父親是個硬漢,吃了再多的苦也從不抱怨。而這政治麻醉的痛苦遠遠超越了他的承受極限。父親只是說,醫生的每一刀他都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次翻動內臟都是揪心裂肺的痛。對父親來說,那手術漫長,沒有盡頭。那強大的黑色痛楚如深淵般地把父親吞沒……,但醫生的下一個動作又如海浪般把父親從海底深處高高地拋起,一浪一浪的折磨彷彿要把他身體里所有的力量、活力徹底捲走,把他的意志徹底摧毀。手術后的六個月里,父親都無法安睡,一合眼就被抬到了手術台上去重溫那一幕,重新體驗那被徹底清醒著開膛破肚的夢魘。
醫生當然知道試驗徹底失敗了。但黨性輕而易舉地就抹煞掉了人性。父親的手術從始至終沒有得到任何一點兒麻醉劑的幫助。沒人知道他們的報告是如何下的結論,是否將此手術的針灸麻醉列為是「偉大領袖英明遠見」的又一次勝利。我也不知道在那樣的年代里還有多少的年輕人也被迫接受了這種政治麻醉並把他們的故事講給下一代人聽。而我確實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而且就發生在自己父親的身上近四十年而不知。是什麼樣的恐懼使得這個家族的故事埋藏如此之久?我覺得我有義務把這荒唐的故事留在紙上,留給未來的人,我們不能輕易忘記。
父親的親身經歷使我不得不相信這種曠古未有的罪惡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為了維護其統治、狂妄瘋癲的獨裁者,見死不救、見利忘義的醫療系統和職業道德淪喪的醫生們都為這種罪惡開了一路綠燈。從死囚抑或是良心犯身上劫取器官,對那些眼中只有利益、心中沒有天良的人來講,難道還有什麼區別嗎?
神州良知不醒,道德不興,巨龍永遠無法真正騰飛。
文章來源: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