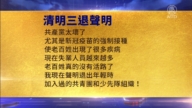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訊】
1
淡忘是人類的通病,荒野蒼生尤其病重於淡忘。花開花落中,仍記得郭泉先生者,或已三三兩兩了。郭泉教授爲了他的社會理想,在兆載永劫的黑夜,同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霧鎖之地竟要被幽禁十年。他老邁的母親,他幼小的孩子,他霜後的夫人,將如何熬過這十年?
我和郭泉先生從未謀面,所有的交往,僅限於通過幾次電話,以及在網上有過屈指可數的幾次交流,但我對郭泉先生的印象,依然是刊心刻骨。在沈寂的午夜,我的耳畔有時會響起他堅定、從容的聲音,他的所作所爲,以及他寫下的一系列文章,迄今還鮮活在我的記憶裏。
2
郭泉先生是在2005年首次走進我的視野的。當時傳媒報道說,日本有人爲明代倭寇王直在其家鄉修建“芳名塔”,郭泉教授和浙江某學院的一位教師夜赴安徽歙縣,把漢奸墓碑和“芳名塔”砸了。我覺得他們的行爲不無莽撞,但在寫作時評時,還是肯定這是一種愛國之舉。
那時我的文字,十之八九能在國內的多家報紙發出,兩大“權威”網媒和三大門戶網站,也常選用著我的文章,故此那篇文字當時也曾“熱銷”。那之後陸陸續續,我在網上看到郭泉先生熱心于“保釣”,於是便也默默記住了這位愛國學者,但其間再也不曾爲其寫過什麽。
3
家破人亡後,我在國內竟再也沒有了言說處,寫了文章得“翻牆”拿到“敵對勢力”的網站去發表,就此便也有了與郭泉先生的“重逢”。於是知道了他在“組黨”,並看到他在境外網站連篇累牘“反黨”。郭泉先生的登高振臂一呼,當時讓許多人依稀看到了荒野的希望。
後來在電話中以及網上交流時,我們才互相知道,我在閱讀著他的文字,他也在閱讀著我的文字,並且常在心中暗暗爲對方的主張叫好,也算是在網上“神交”了不短的時日。我們爲荒野的種種現狀而歎息而傷懷,知道要讓無序的荒野變成有序的園林,或有悠遠的路要走。
4
高估最終還是讓郭泉先生付出了代價,他的身陷囹圄,與他的高估應該不無關聯。他的電話當時一樣重音明顯,但他不以爲意,反而聲聲寬慰著我。我當時客居他鄉,聲明退黨之後感覺自己若釜底游魚,也覺得危險同樣在步步向郭泉先生逼近,於是不忘囑咐他要多加提防。
他卻淡然說,他們應該不會這麽愚蠢,因爲若真那樣做,等於是在將我們推向未來國家領導人的位置。我感覺他在黑暗中未免高估了對手,但出於禮節不好堅持己見,只能反復對他說,一定要記住:政黨和政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郭泉沒想到,夜色竟然真能這般濃黑。
5
郭泉先生以各種形式幫助過許許多多的訪民,我也是受其恩惠的一個。記得那年我夫婦倆在京上訪,路經天安門廣場時,只是因爲身上帶著一份寫給溫聖人的申訴材料,就被惡警扣押,並給投進了馬家樓。在被扣押後,我立刻想到了郭泉,於是用手機向他發出了一封短信。
這之後我就不時接到傳媒的採訪電話。後來有海外人士告訴我,郭泉先生得知我夫婦倆在京上訪被扣押,在Skype上表現得不無焦急,第一時間就向媒體做了通報,要求大家以任何可能的形式“趕緊救人”。訪民在京被關“集中營”多有驚無險,但我內心的感激會綿延終生。
6
我所知道的郭泉先生,以及我與他曾經有過的交往,就只有上述這些,雖然平淡似水,但這並不妨礙我在漫長的黑夜中,時常會想到我記憶中的那個郭泉。現在可能已經很少有人還記得孔強了,我與他曾有過一次通話,但我一樣還記得孔強。有些人,值得我們銘記到永遠。
在我的感覺,仿佛是一個不曾謀面的朋友,爲了公衆的利益或福祉,肩挑了他所不能擔負的重擔,于荊棘滿途中走進了霧暗雲深,不知何日能歸來。我希望自己可以遠行時,能去看望一下郭泉先生家中白髮蒼蒼的老人,想借此讓其感到在人生最後的時光,並不十分的孤零。
嗚呼,郭泉教授!保重,郭泉先生!但願你重見天日之時,就是春花爛漫之際。讓我們在風光旖旎、井然有序的公有園林門前,把酒臨風,等你歸來!歷史和人心,必將爲你準備掌聲和鮮花。天下從來就不曾有過白坐的冤獄,在你此刻受難的荒野,來日一定有鮮花的盛開!
寫於2011年9月19日(廖夢君同學慘烈遇害于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偉光正”與絕人之後的惡魔連袂共舞第1891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動當局連續斷網、斷電視192天!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相關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國家機密”!作家廖祖笙在國內傳媒和網路的表達權被党國非法剝奪!廖祖笙夫婦的出境自由被“執法”機關非法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