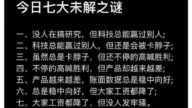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新唐人2014年2月4日訊】這個親戚也是50年代生人,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後來80年代末期京城那件事,他也參加了,當時他尚未退伍,是以一個部隊軍官的身份參加的。意思就是,他去鎮壓了。
起初大家並不知道他參加過那件事,他母親只是懷疑他去了,問了幾次,他起初不說,但後來日子久了,他才承認。據他自己說,說他去的時候已經結束了,根本沒看到什麼……這話是真是假,姑且不去研究,我並不是想聊他參加過什麼。
他轉業時,我還沒上小學,當時他從部隊帶回家很多好東西,子彈啊,彈卡啊,軍帽啊,國徽啊,紀念章啊,軍用望遠鏡啊(這個玩意兒最帶勁),軍裝啊,甚至還有手槍。
由於這個原因,我從小就很崇拜他,出門跟小夥伴鬧騰時候,總是吹噓自己有個“安扣”很牛,你們敢惹我我就叫他拿槍來打你們,他會飛,還會72變,比孫悟空都厲害。
他轉業後被安排在市里的機關做幹部。官位雖然不算大,但足可以令身邊的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因為人家不用為房子發愁,不用為生計發愁,不用為醫療發愁,不用為孩子上學發愁。生在大陸,這樣的條件,夫複何求?
怎麼說呢,我現在覺得他並不適合混官場。因為他臉皮太薄,自尊心太強,人又太敏感。我想這可能跟他的身高有直接關係,他似乎只有一米六。但他的確是個聰明人,不然也做不了軍官。
他在那個機關一做就是十多年。十多年一級也沒升遷。和他一個起點的人,很多都飛黃騰達了,而他還是在原地踏步。於是他更加敏感了。心裏最怕的,最在乎的事就是別人是不是看不起他。
我記得剛去市裡上高中時,去他家裏,他的自我保護意識很強。雖然是近親,但他似乎總怕我給他招麻煩。這也不怪他,畢竟他本身就不是個八面玲瓏的人。
其實說來你們可能會奇怪,他這樣一個標準TG,思想卻很西化。最喜歡對我講的就是,人要靠自己,要獨立,你將來可以去美國混呀,諸如此類的東西。並且我發現他最嚮往歐洲。
而他的立場是絕對不含糊的,至少在我面前從來沒有含糊過。畢竟他是我們口中常說的官員,怎麼可能不擁護自己的社團。
我去他家看他時,我們閒聊,難免會聊到社會上的一些現象。比如市裡的一些黑惡勢力做壞事啊,他們撈了多少黑心錢啊,附近的誰誰不幹好事啊,哪裡前幾天又逮住個小偷啊之類的,他總是很正派,會批評那些當事者:有手有腳不幹好事!真不要臉!而每每聊到臺灣問題啊,對日關係啊,民族局勢啊之類的“大話題”,他更是一身正氣,立場鮮明。我一直都挺不忿他,覺得他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他也總教誨我,要我走正路,別好高騖遠,別聽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瞎說,要我自己更不要瞎說。
但是2011年的一件事,令他改變了。
那年我還在東莞,並不知道家鄉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我上高中,也就是那個親戚所在的城市發生一起詐騙案,全城百分之90的人都受騙了,而且是血本無歸,賠光了一輩子的積蓄。我的那個親戚也沒能倖免。
你可能納悶了,這騙子該多高明啊,能把整個城市的上中下流社會的人全騙了?那些被騙的人中不乏精明的個體老闆,神通廣大的企業家,和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你想想,全城百分之九十是個什麼概念?
其實我把事情簡單一講,你就明白了。
那是個北方城市,市民大多是吃公家飯,即便個體老闆,他的家裏也肯定有國營機關的人。意思就是那裏的人吃公家飯吃慣了,對公家有歷史性的信任和依賴。而那個騙子集團正是拉攏了那個城市的一把手、二把手,以國家的名義做宣傳。說國家要搞一個什麼項目,雖然項目穩賺,但是缺本錢,誰現在能入股,誰將來吃香的喝辣的,利息大大滴……你懂的。
市民一看是國家搞的,那還擔心什麼,投資吧。於是有錢的出錢,沒錢但有野心的借錢出錢,窮人出十萬二十萬的小錢,富人出成百上千萬的大錢。國家號召的,怕什麼嘛。
結果案發後,那個城市的河裏三天兩頭漂死屍。全是血本無歸的自殺者。
我那個親戚本身就節儉,心眼細,從我對他的描述就可以猜到,他是那種本本分分的,小心翼翼的,從不敢大撲騰大鬧的人。所以混那麼多年官場都沒能升遷。他雖然過的滋潤,但他的每一萬塊錢都是積蓄的。我沒敢問他投了多少,但我2012年在東莞聽說這件事時,給他打電話,發現他說話的腔調都變了,似乎有點神經兮兮的。當然了,不是精神失常,沒那麼嚴重。我的意思是,人在受了很大的刺激後會出現的狀態。
案發的原因是,那個案子的策劃者把N億鉅款揮霍的差不多了,起身跑到了外地。然後又被抓回去了。我猜,只是猜,那個城市的一把手二把手和他商量好了,他頂一條命,然後我們兄弟二人保你的妻女平安,甚至還可以祝她們孤兒寡母過好日子。——這個主犯是替罪羊。
在行騙時,幫你宣傳的大老爺不會白白給你宣傳吧?那N億鉅款你分我們多少?——我覺得搞不好都是平分的。當然了,這也是我的猜測,但他們沒少分成是肯定的。
然而你猜這個案子破案後,公家給了全城百分之90的受害者什麼交代?
案發後,全城人成了窮光蛋,天然氣公司都關門了,因為把資金全投進去了,沒錢運營。很多人連那個年都沒過成。
大夥兒不幹,在大年初一(或者是初二,記不清了)聚集在全城的公共場所,把路都堵嚴了,要公家給個說法。
結果公家先是安撫,然後表示錢被他揮霍光了,我們也沒辦法。市民們哪裡肯依,那可是攢了一輩子的血汗錢,那可是孩子結婚上學的錢,那可是一家人下半輩子的依靠。結果大家還是不肯散去。然後公家煩了,開始教育人,說你們自己貪心不足,能怪公家?做人要講道理,又不是公家拿了你們的錢,你們找公家要個什麼勁兒!
大夥兒一聽,急了,說怎麼不是公家,那時候可是你們公開弄的啊!那時候……總之是有理說不清。人們還是不依。和上面有關係的開始托關係(別忘了受害者還有八面玲瓏的企業家),有人的開始托人,有種的開始帶著乾糧進京。
公家一看局勢要亂,那維穩吧。派了威武雄壯的人民子弟兵,封鎖各個交通要道,“勸說”要進京的人——倒是真沒有發生什麼暴力衝突。人民子弟兵多親切啊,有他們勸說,誰還能去得了京城?再說了,即便你去了京城,這邊電話一打,你剛下車就會被接回來。
我那個親戚那天也參加了。不過這次和他當兵時那次略有不同。身份不同。不曉得他當時看到子弟兵來勸說自己時,心裏是個什麼感想。
我還有個表兄(就是我那個親戚的侄子,由於趕上了計劃生育,那個親戚只有一個女兒,所以他施展關係把表兄弄到身邊,意思是將來老了有個指望)雖然那個親戚和我在一塊時總說閒話,不會聊真格的,但他和我那個表兄可是掏心掏肺,不會太隱瞞,畢竟拿來做親兒子的。我清楚這一點,所以和那個表兄通電話時,無意間聊到了那個親戚的態度,我問表兄,”安扣“沒事吧?賠了那麼多錢。表兄說,咋能沒事呢!對了,你可千萬別問他!別再跟他提那件事!這段時間剛好了些,你一提他又該犯病了。說完這些,表兄又開始嘮叨,說可真把人坑得不輕,可真把人坑得不輕……——他自己也把積蓄投光了。
我問他,那公家怎麼說的,給賠多少?表兄一聽,又激動了,說:”要給你賠呢,人家投了幾千萬的,過年才給了400塊錢。我們這些小投家,一分也沒有。“說完,他又接了一句:”共產黨辦事……嘿嘿。“我問他,怎麼你現在也對公家有意見麼?——他也是公務員。他說肯定啊,現在誰對公家沒意見?我說,安扣肯定就沒意見,他自己就是。表兄說,沒那個人!他也是罵,在家生悶氣,拍桌子罵。我試著問,罵公家?表兄說了個嗯。然後我們又聊了些其他的事。
那個案子是這樣處理的:所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公司企業內的人,如果你不服從判決上訪的話,那你將會被開除,個體戶吊銷執照,學生勸退。——不曉得乞丐如果不服,會不會被吊銷行乞證。總之,他們的錢血本無歸。
我個人認為,這個國家最大的病根本就不是貪腐,而是從來都沒尊重過任何一個人。這個國家最大的病就是人們互相踐踏,缺乏同情心。也可能是有同情心,但面對阻力時,卻不敢堅持那份同情。——說白了就是喪失了人性。
你看看這幾年被斬首的官員,一個個什麼下場?當需要你時,讓你吃香喝辣,縱容你做一切惡行,當需要你去死時,刀砍下去不會眨一下眼睛。根本就是拿你當狗!還是農村的土狗。城裏人的狗幾個人會殺了吃?而農村的土狗,在幫主人看了一輩子家,在垂老之後;腿瘸了之後,主人厭煩了之後;主人家生孩子怕孩子被嚇到的時候;主人家沒有任何原因只是不想養了的時候,都可以毫不猶豫地把它扒皮拆骨,油烹水煮。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活得很好,覺得我是在說廢話。沒關係,總有一天,你會想起我這個親戚的故事。到那一天來臨時,希望你坦然,因為這不能全怪別人。
這個故事我從未對身邊的人講過。因為他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做狗,而我想做人,我不能一直對狗講人話,這樣會被狗歧視的,這很令人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