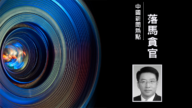「夜夜難以入睡,幾乎天天半夜驚出一身冷汗,醒來就再也睡不著,總想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開會,怕在會場被帶走;上班時怕回不了家;上級領導約去談工作,也怕是借題下菜。開會時在台上坐著,往往心不在焉,只得強打精神撐著;一個人時,唉聲嘆氣,多次用拳頭敲打自己的腦袋,發泄胸中壓力。」這是濟南市委書記王敏寫在《懺悔書》里的句子,非常形象地為我們描繪出一幅現任官員的生存圖景。
這是瀕臨絕望的狀態,比「熱鍋上的螞蟻」更甚,或許可以稱之為「末日焦慮」:審判總要到來,不管誰是審判者,貪贓枉法的官員都自認是罪人。善意的理解,他們彷彿也一直期待終結的時刻,——在泥潭裡固然恣意快活,但於慾望極度滿足的背後卻也隱藏著極度的不安——因為一場戲總要落幕,如此胡作非為無法無天的權力狂歡,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懲罰。他們明白,儘管整個權力監管系統失效,但天譴還在。
只不過,在審判降臨之前,他們大多懷有僥倖心理,總覺得自己不會是那個倒霉蛋。基於絕對權力而來的自負,讓他們陷入某種愚蠢而狂妄的狀態:誰也不可能知道我的作為,大家都是如此行事,只要不得罪權力授予者,其強大的庇護絕對能擊敗敵人;我們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一亡俱亡,除非日月翻轉,可怕的系統性崩盤才會發生。
在此之前,我們能感受到官員的焦慮和不安,但沒料到他們已處於如此惶恐、近乎神經質的地步。可憐么?可憐,但活該。
一個官員怎樣才能將自己置於這種境地呢?
不言而喻,他做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斂財獵色到了相當瘋狂的程度。一般的貪官小吏也擔驚受怕,也會恐懼,但絕不會到達如此程度。大恐懼出於大放縱,一個貪腐高官擁有的權力,是官場之外的人所無法想像的:他在一人之下(名義上往往是一個神聖的組織)、萬人之上,他所擁有的權力讓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有如此權力的人的作為,在他所管轄的領域,他就是王。他一言九鼎,他說一不二,他生殺予奪。轄區內的一切生靈、田野、道路、天空都是他的。當他坐在權力寶座上的時候,他豈能不顧盼自雄不搖曳生姿!每時每刻,他都在享受人生的高潮。
在東窗事發之前,他們往往竊喜於一己之高智商,將自己視為此種社會制度下最善生存的生物。這讓其高估了能力和關係,低估了正在聚集的風險,系統性風險讓他們措手不及。他們是無規則社會的最大受益者,同時也是最可悲的受害者。
這位書記的自白,或許隱含著許多水分,因為他會刻意誇大自己的恐懼,企求獲得態度誠懇的認可,既能博得審查者的同情,也能獲得國人的諒解。這大約是一種事後的自我分析,而分析往往都是以極端的方式出現的。人們會想,身心處於如此緊張、焦慮的狀態,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又如何可以一天天熬下來呢?被擒拿之前,儘管也焦灼難捱,但他們擁有頤指氣使囊括天下萬物的高峰體驗,那是常人所無法體會的樂趣,所以,他們寧願誠惶誠恐地高踞權力之位,而不會決然歇手回頭是岸。
但他們的害怕是真實的。在握有生殺大權的欽差大臣面前,他們幾乎處於無保護的地步,弱小無助,苦衷又無法向外人道也,只有自個兒明白自己做了多少淫邪之事,他們知道自己將會隨時被執,自此身敗名裂,他們面前只有一條通向地獄的道路。但還是害怕,在落馬之前,巨大的無法違拂的陰影籠罩著他們,出於生理本能的恐懼油然而生。
一個絕望的官員,他的人生還能有別的出路么?僥倖,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最後一把稻草。
一個敢死的官員一定被巨大的恐懼攝住了靈魂,他不願意看到自己苦心經營的局面坍塌,知道會,但不願意麵對或承受——雙規,審查,樹倒猢猻散,建立在貪腐惡政之上的帝國轟然瓦解。他寧願活在幻覺里,而死亡讓他們保留了這個美好的記憶。一個個獨立王國的崩潰,已經不能讓沉默的百姓產生更多的快感了,他們早就放棄了對公平正義的奢望,轉而以幸災樂禍的心態議論這一切。城頭變幻大王旗,無官不貪的現實讓人們心灰意冷:換一個還不得去貪?沒有選票,他們只能充當看客,而看客唯一的武器是冷嘲熱諷。
前赴後繼的貪官,以其言行書寫著人性淪喪的悲劇,他們人格分裂,良知泯滅,非人非鬼,因為他們一直在做自己反對的一切事情。或許會有人問,難道是制度撕裂了人性,使得每一個進入這個體制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蛻變為人格分裂者?
官員們似乎夾緊了尾巴,他們都在賭一口氣,看誰倒霉;如果連我都出事了,那就沒有官員可以倖免了。不作為其實是最明智的策略,有所作為必然開罪於人,被視為靶子,而誰屁股下面沒有幾攤屎呢?
儘管如此,不時有官員縱身一跳了斷自己,這讓人們感到某種透徹骨髓的寒意。跳樓,是精神的崩裂,接二連三地赴死,正在造成空前的恐懼。這恐怕會讓中國的局面更加不可捉摸。若不承認制度造就普遍貪腐的事實,反而以高滔的道德和鋒利的刀刃逼官吏馴順,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自首或自盡。到最後,會不會出現魚死網破的慘況呢?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