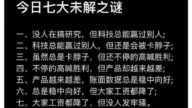父親是個老實的讀書人,戰亂的時代身不由己,年紀輕輕被托付著要留下祖脈的一條根,離鄉背井的逃難到臺灣,眼看反攻大陸的日子越來越遠,回鄉越來越難,再想到祖父身居國民黨地方要津,共產黨不會放過,因此常常滴淚。我自識事以來,他便告訴我他是個「孤臣孽子」,沒有留在中國跟共產黨拼了,對不起國家;沒有盡到孝道,對不起祖父母。
父親帶來的時代氣氛充分感染著年少的我,使我比同齡的孩子早慧。年少的我跟父親說,我不會再當「孤臣孽子」,一切的一切要到我這為止,我不要我的下一代再受這樣的煎熬。父親告訴我不論我受到的教育有多高,將來成就如何,不能忘了自己對中國的責任,不能忘了是共產黨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父親在大時代的錯愕中,馱負著中國知識份子對歷史的使命感,他跟我許多的父執輩一樣,對中華文化精深和高貴內涵的終身嚮往,但是在現實生活裡被共產黨逼得有家歸不得的落差,使得他們在一起常鬱鬱寡歡。
父親常說「臺灣沒什麼好,臺灣最好的就是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滅天滅祖的狼心狗肺」。當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時,我的父母幾乎是趕著第一批的返鄉人潮奔回老家。父親第一次從他的家鄉返臺後悲喜交集,告訴我街坊鄰居都到了,竟還有人知道父親回來了,騎了個把小時的人力車來見他,扑倒在他面前,跪著請父親原諒,說是當年祖父照顧他全家老小,是個大好人,但是當祖父被共產黨抓到街上批鬥,整死在街上的時候,他看到了也不敢在街上收屍,怕受牽連,看到我祖母活生生的被逼瘋了,也不敢上前問候一句,說他自己已經被整的人不像人……他哭著喊著對父親說,他對不起祖父,他對不起父親,他隱忍痛苦了很久,就等這一天要父親當面原諒他。父親抱著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哭成一團,卻也什麼安慰的話都說不出。
鄉里的共產黨幹部也找上了返家的父親,要跟父親打政治麻將,說穿了就是要錢,說父親在臺灣發達了,該回來造福鄉里了,父親為了當地的親友不受壓力,只好虛應故事幾下,心中當然是天大的不高興。溫文儒雅的父親說這筆國仇家恨,中國人想忘也忘不掉。幸運的我沒有過這樣的痛苦,但我知道共產黨在父親和那些長輩心上戳的一刀刀的歷史傷口,深不可測,癒合不了。
父親也有高興的時候,就是教我四書五經,背唐詩宋詞,講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等等,告訴我中國人最好的,最驕傲的資產,就是傳統文化,中華文化不只是給中國人的,也是中國人留給人類的,說小孩子要在沒受世事污染的年紀,多充實文化上的東西,懂不懂在其次,那是我們中國人骨子裡早有的,腦子裡先早早存著老祖宗的智慧,以後就會派上用場。
我從小喜歡咀嚼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學,知道這些文化是造就父親,造就中國人底氣中最紮實的東西,尤其孩提的我看到父親歡喜,我就能跟著高興,就像他所說,中國遼闊風土所孕育出的中國子民是大器而豐富的,江山不求回報,就像父母都想給子女最好的一般。我告訴父親,我骨子裡也有「飲水思源」,我安定的生活是他苦出來的,我要還報與他,還報於民,他說不要好高騖遠,最好的作法,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終其一身,他留給我「清白傳家」四字。
當父親年邁,多次返回老家後,他開始念叨中國變了,中國人也變了,真是被中共糟蹋壞了,文化大革命抄的不止是這一世的家,是真正想拔掉中國先聖先賢蘊積多少個世代留給子孫的根,中共狠毒啊。他說年輕的國民黨沒有經歷過中共的心狠手辣,又沒有歷史使命感,氣的他把黨證給寄回去,卻沒想到寄出去沒幾天,竟然收到國民黨黨部發的獎狀,獎勵他三四十年的優秀黨員,弄得父親哭笑不得,幽幽的說,這群國民黨跟中共合也垮,斗也垮,軟硬都不行,只要跟這些鬼接近了,就等著被吃掉吧。回頭對我說,中共不垮臺,你也歸不得啊,你是不是也生錯了時代啊。
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時,父親謹慎細微的觀察著他唯一的女兒到底在修煉什麼,當他瞭解我沒有隨著人世載瀋載浮,更加誠實、善良及理性時,父親的心趨於安穩。
父親臨終前,沒有對我明講他的骨灰還是想回到大陸家鄉,不想跟著臺灣的我,一方面是怕傷了我的心,再者知道中共不讓我進大陸,我是沒法親自送他回去的,但是身為獨女的我怎能不成全老父最後的一點私人心願呢,在外子協助下,父親還是送回去了。
我很想對父親說:「隻留一層畫皮的中共氣數已盡,幽靈即將灰飛湮滅,中國人的『國』與『家』,即將走入一個新的紀元,我將在這個時代為你見證一個沒有中共的『中國新年』的誕生!」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