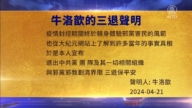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09日讯】在上集节目中,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总结了自杀的两大类型。其中,由于恐惧心理而自杀的人群中,还有正处豆蔻年华的青年学子们。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 我们继续来了解。
据中共《内部参考》记载,50年代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斗争和打击的态度,孤立办法之一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
严重的包括四川大学团委,仅从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到1952年7月,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1952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
另外,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1952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这些学生还被实施各种行动限制。
辛灏年:“年青人经不起这样的折磨。大多数青年学生自杀,就是因为他们被孤立,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父母对他们也救之无能、无力,所以这就属于整个制度和社会给他们造成那种恐惧心理,最后轻视人生,自杀而已!”
反右期间,《内部参考》1957年的一篇报导提到:200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辛灏年:“有人说只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大错特错!我所知道的就有几十个。我最近还为一本书写了序,这本书里面就写了一个华侨学生在大学里被批判,被斗争,然后跳楼自杀的历史。要知道,出身成分不好而被逼自杀,就使得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反动的、黑暗的等级社会,高层阶级是可以逼低层阶级自杀的,甚至进行屠杀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辛灏年表示,还有一种自杀类型,是人格型的。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份子,无法忍受对他人身、精神的恶意侮辱。
辛灏年:“ 比如说,当‘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校园里面贴出来以后,在全校被关的、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结果天天都有人跳楼、上吊自杀的。北大集中了多多少少的学术权威啊?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初期,单单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个。很多人还没有收集到很多资料。上海音乐学院,一共只有二、三百个教师,自杀的就达到了一百多人。”
另一种自杀类型,则是特殊的绝望型的。
辛灏年:“我们讲,自杀的人都是因为绝望才自杀的,不绝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但是在绝望里面还有一种绝望,在普通对生活、生命、人生绝望的背后,还有一种对信仰、对领袖、对政党、对制度、对社会的绝望。在这种绝望的前提下,有一种人被斗争到七死八活的地步,最后只好绝望自杀了。”
辛灏年表示,在绝望型自杀的知识份子中,还有更高层次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绝望,对自己曾经信赖的、赞成的、喊万岁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绝望。比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等。
辛灏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刘绶松夫妇就这么一根绳子,从挂帐子的床架上面挂下来,两个人一人一头自杀的。有些夫妇是同时吃安眠药的。这是一种绝对的绝望,这种绝望远远高于对自己生命的绝望,而是对自己灵魂的绝望,对整个社会、对人类的绝望,最根本上的都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绝望。”
然而,不管这些自杀者如何绝望,身怀多大的冤屈,在中共的眼里, 他们的自杀都不能给自己“免罪”,反而还增添了新罪。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