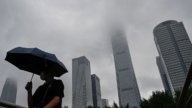【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 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夏明】我想给大家来个比较宏观的回顾,中国治理体系的几十年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毛呢,走向邓,走向赵,然后再走向江,走向胡。我在四川听到我的姐夫给我讲一个笑话,我觉得四川话讲的非常有味道。他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矛盾)的国家,“胡”来不得的,“赵”(照)这样下去,“江”(将)来怎么办?还“胡”来?
我觉得这个笑话概括了中国的治理体系,感觉非常好。我把中国分成四个治理模式,或者叫做范式。在过去的五十年多中,尽管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毛时代呢,包括华国锋的过渡时期,“华时代”是“毛时代”的一个尾巴嘛,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把它叫做“运动政治”。邓时代呢,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它叫做“试验政治”。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和九二年的“南巡”正式标志着“试验政治”的终结。江泽民上台以后,我把它从一九九三年算起,就是说从“南巡”结束后,到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就是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了,我把那段时间就叫做“工程政治”。二零零三年以后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来就是跟温家宝搭档,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时代”的到来,把它叫做什么呢?是“和谐社会”、“ 协商政治”呢,还是要再寻找的一个新的范式?
我在《中国人大制度和治理》一书中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范式,希望能够影响中国未来政治,我把它叫做“磨合政治”,这是我自己提出的范式。通过这一范式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治理趋势、执政目标、执政手段和执政结果都有些差异。同时带来了领袖-官僚-民众的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发生一些改变。这四个范式呢,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中国治理体系和未来走向的意义。
我们首先讲讲毛的“运动政治”。毛建了一个“动员型体制”,将整个社会民众都动员起来,并强迫他们参与到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就像毛所说的,“类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三五年就该再搞一次”。那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运动,我不想罗列了。因为我们讨论得很多,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等等,最后以华国锋“洋冒进运动”收场。这段历史留给中国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昨天刚谢世的谢晋导演拍的“芙蓉镇”里面最后的一幕,王秋赦敲着那个破锣,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这就宣布了“运动政治”的收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运动政治”,又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小时期:毛以军事运动夺得政权,建国后他又试图以同样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一但经济目标失败,毛及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遭到削弱和怀疑后,毛又以“政治运动”来维护他的政权,整合他的政权。这就是毛的运动政治。
邓接下毛和华留下烂摊子以后,我们可以说,邓是迫不得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进入了“试验政治”的阶段。为什么我把邓小平的叫做“试验政治”呢?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有几句话,最好地概括了邓这一阶段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猫论,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三个就是“三个有利于”。邓是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社会已经失序的情况下被逼上了梁山。但有的地方我们也看到,邓从延安经验中汲取了灵感,即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试验-总结-推广”。
由于邓“试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都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邓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既不同于“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也不是他所乐于接受的所谓“总设计师”的定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佳定位不是总设计师。我在二零零零年写过一本书《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书中给邓小平的定位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产士”。“助产士”这个概念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来的。苏格拉底给“助产士”有三个界定,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老人,那么我无力产生新鲜理念了。第二,我可以帮助年轻人接生助产新的理念。第三,如果年轻人产生些狂妄怪异的想法的话,那我就把它给扼杀掉,这怪胎我就不让他接生,我就把他扼杀。如果用“助产士”这个概念来观察邓小平的政治作为的话,我觉得他的两大手笔,所谓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沿海特区的建立,邓的角色都不是“总设计师“,而只是“助产士”。里面的细节呢我就不多讲了,万里和赵紫阳在农村搞改革,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搞特区。
如果我们再看邓小平这一阶段最后的两项作为:“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邓又承担了所谓“怪异思想杀手”的角色。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遗产。这政治遗产也就是吴国光所说的,“两个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政治专制。”
我觉得,如果仔细看这两笔精神遗产,会发现它们是有不同针对性的。我把八九年天安门的屠杀定位于:邓小平给中国人上了很大的一堂课。天安门这堂大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同年拉萨军事戒严的一个延续。或者说这是一次补课。那它主要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对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地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诉求进行扼杀。也就是传说的,邓小平不惜十万生命换取十年的稳定,这个就是他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
如果说八九年镇压事件是给中国老百姓的大课,那么九二南巡就是给江-李班子的一堂小课。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接班人呢,从智商上面来说是相对邓小平要低一点。尽管邓小平也有很多可以非议、批评、指责的地方,但是在这四个阶段中,邓小平恐怕是中国人最好的一个领导。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待会儿我们一起讨论。邓小平利用深圳这个“试验政治”的重要平台,向他接班人发出了最后通谍,“发展就是硬道理!”“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在他“试验政治”的早期,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旨谕是:政治上我给你们撑着,经济上你们大胆地去闯。他对深圳的期望是:作为试验田,作为特区,你们大胆地去探索,为中国经济闯出一条血路。后来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系统地提出了“试验政治”的更多设想。但六四和南巡事件后,邓对他的接班人说,“不争论了,我们应该集中抓经济建设”。邓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为中国政治发展找到了药方。这药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软市场、硬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模式。他也提到了要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或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新加坡。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明确的发展计划,这就标示着中国“试验政治”的结束,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
我怎么样命名中国进入的这个新阶段呢?邓小平自己定位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赵紫阳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总执行官,而江泽民给自己找了定位,他说“我是这个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六四”镇压和九二“南巡”后,邓小平已经结束了他的“试验政治”,自信地认为他为未来中国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一下就给中国任命了两位总工程师,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来执行他这个路径,确保他给中国指的路径不被打断,也就是来维持、运作他的专制发展模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工程政治”的模式。
江泽民整个“工程政治”,从人事安排上来看,最绝的就是他就职的时候,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都拥有工程师的头衔,“清华帮”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独特风景线。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人,还在于思想。在苏联模式强烈影响下的“技术官僚”,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导,以生产力论为中心,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在这种心态下,任何的政府作为都是冠以“工程”之名,所以有很多形象工程、工程一上手马上变成民心工程,马克主义工程等等。我把他叫做“工程政治”。“工程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政府把老百姓作为一个大工程的螺丝钉和机器零件运作。它把政治界定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有确定的答案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政治”出现的最大悲剧,就是对教会的镇压,对人精神的持续镇压,包括镇压法轮功。这就是“工程政治”最大的弊端。
二零零三年后,我们看到“胡温新政”提出了所谓“科学发展观”,他们所做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工程政治”进行新的微调和新的改进。说到底就是中国政治应该怎么走的问题。胡温提出了“协商政治”,那么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以“和谐社会”为定位目标。但是很不幸地说,今天的胡温政权,把“和谐社会”不仅仅界定为理念和目标,而且把它作为施政的手段,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因此就不允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以这种手段来统治中国社会。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手段,那么“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有允许百姓通过上访、游行、群体性事件等低层次的冲突,在动态中,和谐才会产生。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胡温在镇压机制上投资的代价有多高。五月份我跟一群电影制作者到四川灾区去,我们被十几部警车围住,还把我们扣留起来,进行审讯达八个多小时。我们沿路拍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拍我们的人比我们的摄影师还多,有特警有便衣,有穿警服的摄影师等等。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想为“胡温新政”开帖药方。去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人大与中国治理’。在这本书里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透过摩擦才能产生和谐,如果不允许摩擦的话,是永远达不到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有太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百姓的暴乱和宗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绝于党国的老百姓。
很多人的确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但他可以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可以是一个车友会的组织者,他们远离政治,就已经然国家的触角短路。另外的群体性事件、宗教信仰团体的反抗从底层和民间就能够对中国政府施压。通过这种摩擦、这种动态的冲突,才能够制造出未来中国的政治和谐,所以我把它叫做“磨合社会”。我把中国的这几个治理模式讲清楚以后,现在就要总结下这样说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我在思考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吃人的怪兽。首先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吃掉了自己的敌人。政权建立后,它又在维护政权的名义下,开始吃所谓的政治异己者,就是他所谓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国民党暗藏的特务等等。然后就吃自己过去的盟友,通过公司合营、利用反右等等,把这个过去的盟友给吃掉了,如资本家、知识份子。盟友吃完了以后,他开始吃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成千上万的在大饥荒中被饿死。接着,又吃自己的子女,先是在文革中让自己的子女发狂,然后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将他们驱赶到农村,遭受非人的折磨。这一过程也延续到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后来的“六四运动”。从文革开始,它不仅吃自己的子女,也自残手脚。
那么就是说为了维持他的政治大脑,他开始舍弃自己的手脚,他开始蚕食革命同志,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许多的所谓的贪官污吏成为这个“政治怪兽”的饲料。最恐怖的就是江泽民时期了,在反腐败的名义下,通过枪杀和关押而镇压共产党官员的比例比毛泽东时期要多的多。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人自绝于党国那是一大幸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身陷囹圄或者去死,不愿成为那个政治绞肉机吃人链条中的一部分,不愿成为一个专制社会的殉葬品。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恐怖的逻辑。
第二,我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政治败血症。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记得曾在马来西亚参观过当地的民主博物馆。在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像前挂了两幅像,一个是林肯,一个是温士顿•丘吉尔。无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多么不完善,但他们的模仿对象一个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个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摧毁了法西斯极权政府、捍卫了民主。但是我们呢,中国领导人挂的是马列斯毛。而斯达林跟毛泽东作为历史的罪人,这一定论在政治学界是毫无疑义的。另外,我们在讨论中对于马克思没有进行任何的批评,其实他最可恶的就在于,他还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首先要改造人类,要把每个人改造成有高度觉悟和认识的品德高尚者,然后再去实现他的理念。试图把人性维持在高水准的想法反而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人间惨剧”。
第三,就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和“渐进的社会工程”之间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卡尔•波普尔批评专制社会、封闭社会,认为最最可恶的东西在于大搞社会工程,也就是我说的“工程政治”的运作。因为喜好大工程,就不允许小规模渐进的社会工程发生。在他垄断政治参与权的同时,也就阻止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应该进行怀疑的是这种宏大的社会工程。
第四,中国否认人性的多元性。当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断地讲着吃饭政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人当作动物对待去,把吃饭变成人的全部。而我们认为,吃饭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他不是人类的全部。如果要说人类本性的话,至少包括“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只有承认多元性的情况下,人的价值才不单单停留在工具价值的层面,人的“命价”才会提升。中国在地下教会和法轮功要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它就来镇压了;当许多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想说真话,想做有道德的人士的时候,它又开始镇压了。所以中国人的“命价”就非常的低。低到我们只进行一种生物层次上的满足。而至于其他的人性追求,国家都是可以剥夺,可以扼杀的。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恐怖的地方。
最后一点是关于人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人的价值,只当作一个使用价值,它没有想着人的本体价值。我说的“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那就是人的整体价值。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必须用个人主义,个人价值来对抗国家主义。中国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一个钻石的格局。从奥运会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结盟。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最基础的个人主义来对抗它。为了抵抗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全球主义来对抗它。尤其是在范式重建问题上,我觉得必须得考虑这么一个钻石的结构。
最后讲一讲老子学院的问题。中共在全球试图总共建立500来个孔子学院,每个学院要花一百万进行建设。而我就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老子学院。希望用民间的力量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跟他的孔子学院对抗。为什么呢?因为从老子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对神的崇拜,对来世的追求,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小政府的期盼,对大政府的遏止,希望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一所民间的中国文化中心,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多元解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夏明,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现为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 (获终身教授资格)。复旦大学访问教授 (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讲座研究员。 参与过«社会学概论» (1992年高教版)和 «比较政府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的写作, 著有:«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 »两书。现正从事《中国黑社会三部曲》(英文)的写作。
新唐人首发 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听打:李菊芬